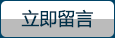免費電話:400-0371-282
企業QQ:400-0371-282
普通QQ:707134090
移動電話:15803856648
地址:中國·鄭州 航海東路富田財富廣場2號樓22層
企業QQ:400-0371-282
普通QQ:707134090
移動電話:15803856648
地址:中國·鄭州 航海東路富田財富廣場2號樓22層
右腦百科
讓孩子在情商教育中受益
更新時間:2014-02-27 17:24??瀏覽次數:
社會的壓力讓大人不得輕松,在這種壓力之下的教育,就是讓兒女不會溝通。我相信諸如“槍打出頭鳥”、“夾起尾巴做人”、“沉默是金”這一類的“諄諄教導”,并不是出自什么名人名言,而是父母之口。父母習慣一邊給孩子樹立太多的條條框框,一邊意味深長地對著稚嫩的幼子總結他們的多年經驗,說,多聽話,少說話,想法要務實,做人要踏實。
可是好多人并不是這么說的。
反正莫言不是這么說的。
莫言說,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,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、安穩大方的孩子。但在我身上,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極大的說話欲望,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,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。
反正童話大王鄭淵潔不是這么說的。
鄭淵潔說,我每天都要給自己幾個小時的時間,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,就是胡思亂想,比如把自己想象成外星人,想象自己是一顆牙齒等等。想象已成為我賴以生存的方式。
反正著名導演馮小剛不是這么說的。
馮小剛說,創作不外乎兩種方法,一是靠一群聰明人坐在賓館里搞"頭腦風暴",另一種是笨人笨辦法,就是靠兩條腿走出來的,沒有故事,就要到現實中去找故事。
看來,父母從小的教導不一定都對。
問題出在哪兒了?我覺得關鍵的問題在于家長的關注點不同。
因為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,所以身為60年代的父母,對待80年代的子女,就是衣食住行的照顧,并不在意孩子本身才智的培養;因為經歷過下崗的波折和下海的動蕩,體會到了社會的競爭壓力,所以身為70年代的父母在意90年代的孩子自身技能、等級、考試能力的培養,卻忽略了孩子的心智培養;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變遷,“素質教育”漸漸地從流于形式轉化成家長真正關心的話題,心智的建立和情商的培養,顯然比孩子的物質比拼和分數的高低重要得多了。
曾經看過一個報道,日本人教育孩子的方式,是擔負起自己的責任,一家出門旅游,各自負責自己的行囊;是鍛煉自己的體魄,冬天穿上運動褲短跑;是培養自己的膽識,堅持讓六七歲的孩子走夜路回家。。。。。。孩童有無限的潛力,是因為他們有無限成長的可能,這種成長,需要對他們天馬行空的想象給予鼓勵,需要對他們錯誤的嘗試給予寬容,需要對他們的自身素質給予激發,需要對他們的言行給予指導。
六七十年代的孩子,可以坐在高高的谷堆旁邊,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,對他們來說,這就是童年;八九十年代的孩子,手里玩兒著各種玩具,偶爾唱上兩句“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”,也算是有了自己的童年;到了二十一世紀,看著如今的孩子被毫無教育意義的低級動畫和電子游戲包圍,他們說這是他們的童年,我卻覺得這是另一種紙醉金迷。
你孩子拿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拼成績、比智商?你out了。想要讓自己的“寶貝”真正的成為寶貝,有更多的情商教育等待我們去挖掘。本文由中國全腦開發網整理發布!
- 上一篇:母親對孩子的一生有著重要的影響力
- 下一篇:正確認識什么是早期教育